《缓步》
加入时间:2025-03-24 14:29 访问量:1210 信息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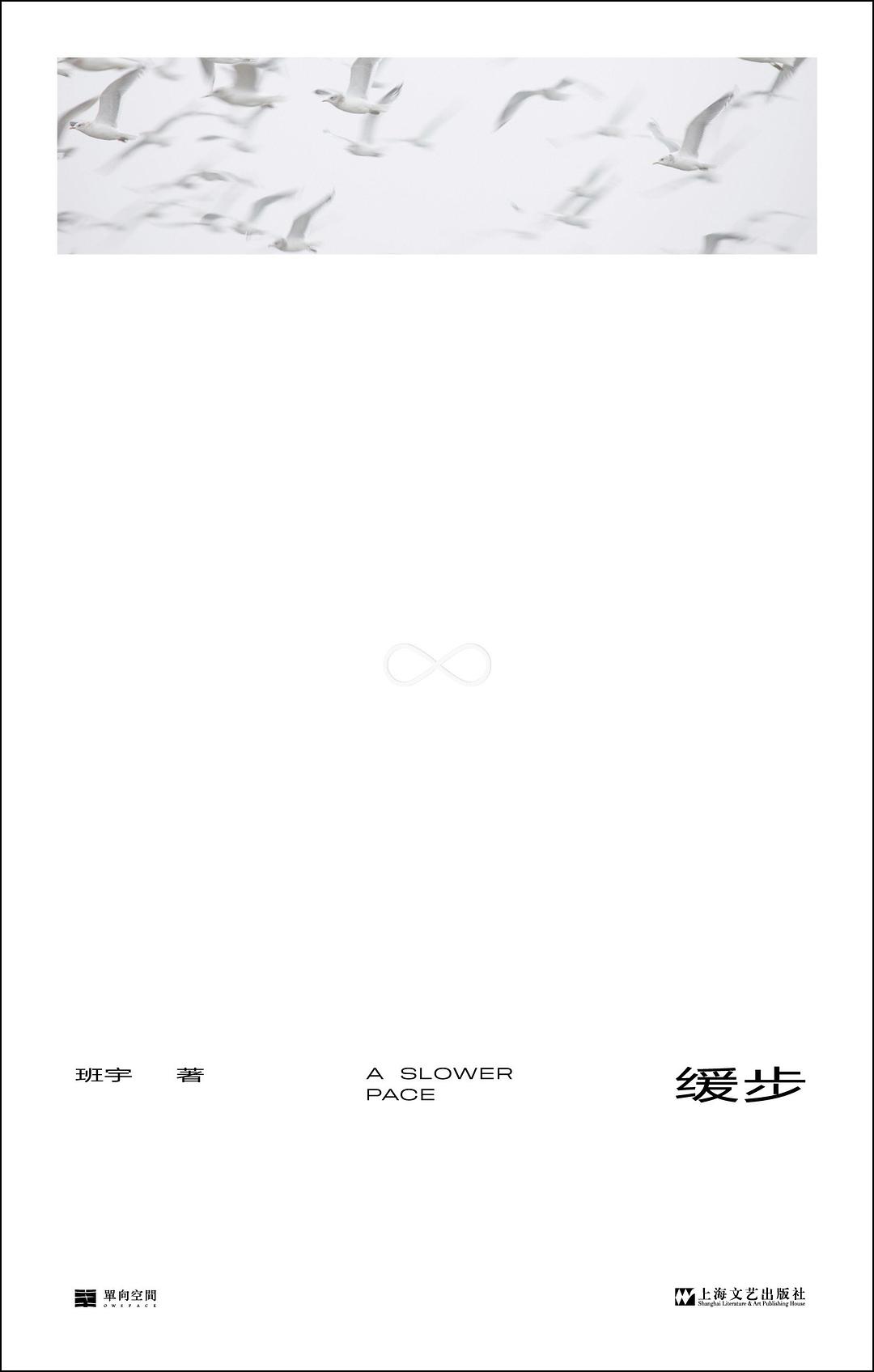
责任者:班宇著
索书号:I247.7/5004
《缓步》收录了班宇的九篇小说,除《活人秘史》抹平区域和年代,其余几篇均提到破碎的婚姻,以及人在婚姻中的背叛与报复,辜负与懊悔,其背后皆有家庭负累,或是父母,或是子女。无可挽回的婚姻,无可追溯的记忆,无处安放的慰藉,无法挣脱的负累……这正是中年人的难以逃脱的困境:一边受罪,一边疲惫。
令人欣喜的是,《缓步》褪去了《冬泳》《逍遥游》被贴上的标签,期待读到班宇东北故事的朋友,或许会再次希望落空。
在这本小说集中,班宇的叙事更加娴熟和从容,他却不再止步于故事与人物本身,而是毫不留情地揭开皮肉,直面血淋淋的内里,以敏锐的洞察深入人的幽微之处,将中年人的疲惫、困顿、挣扎、反抗给予精准刻画。这让事业上困顿、家庭中胶着的我们,更深地被刺中,被揭穿,被抚慰。同时,他在先锋实验中的自我指涉与反噬的冒险,让我们以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残破不堪的人生。
活受罪
《我年轻时的朋友》中,邱桐这样解释“活受罪”:不是活着就要受罪,而是得去感受我们的罪,这样才算活着。《漫长的季节》中,“我”自问:我们所受过的罪,哪一种不是白白浪费?人难逃受罪的命运。因而,在书中,我们很强烈地感受到,一切负累都压得人直往下坠,人自身也是负累。
书里有很多描写人在困顿中前行的场景,或是现实,或是梦境,在洪水中挣扎前行,在河水里茫然前行,在人群中竭力前行,在黑暗里摸索前行……我们常被一种存在主义观点误导,认为一切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你是你的选择。脚上的泡是自己磨的,受罪也是自己的作的,即便命中注定,也可解释为前世所累,此生赎罪。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人迹罕至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因此,小说中的人物都将自己像蚕一样裹在茧中,以疏离的眼光面对受过和即将遭受的罪。正是在这层包裹下,我们疏离了与他人的关系,致使情感破裂,而我们的冷漠和言语的乏力,又导致破裂之不可修复。
《我年轻时的朋友》中,“我”对以前的事情既不惭愧,也不淡然,而是毫无感觉。《缓步》中,“我”承认,我们的伪装与冒犯,只是为了不被俘虏,成为“灰溜溜的人”,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痛苦、神秘与真实,也无关奉献与亏欠、忠贞与背弃,而源于生命本身的不可弥合的裂隙。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体悟到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罪”,由此摆脱对“自我”沉溺,如《缓步》中的“我”,在与女儿的紧紧依偎中,不再有愿望,也不再想去拥有自我,最终聆听到来自更广大世界的清澈鸣叫声。
《透视法》中,“我”在考试时发现,时钟秒针每前进七秒就倒退一秒,可见,未来、当下是在过去的裹挟下走向未来的。我们无法摆脱记忆,时常会梦见过去的荣光与恐慌,包裹在记忆中的“罪”,也无人能够逃脱。那些试图逃脱的人,如《我年轻时的朋友》中的邱桐,《缓步》中的小林,《漫长的季节》中的闵晓河,《凌空》中沈晓彤和余林……都注定会沦为“灰溜溜的人”。
世界就是一个洗衣机滚筒,我们无处可逃,也无人生还。
这绝非悲观之论,而恰恰是对人的精神的首肯。正如书中所说,记忆是“空虚之锁”,人的精神是钥匙,能汇合过去与未来。只不过,悖谬的是,逃离过去,精神就会萎靡堕落,陷入虚空的深渊;直面过去,便会让罪绑缚,呈现出中年人的疲态。
缓步台
班宇用很多笔墨描写中年人的疲态,如“灰溜溜的人”“吸附在岩石、荒野与海洋上的一堆无机物”“寄生的植物”“投入诸多的努力,只是艰难地维持着普通与平庸”……
《羽翅》中,马兴重病的父亲,不想因咳嗽毁掉自己一生的严肃形象,只喝小米粥;《漫长的季节》中“我”重病的母亲,自尊心极强,口齿不清后,索性一句话不讲了;《缓步》中,小林出走后,女儿木木只想让人听见自己说话,不再渴求倾诉能够得到回应……人受罪的同时也在维持着自尊,此重任落在中年人肩上,而中年人自己的尊严却危于累卵。人只活一次,只能经验人生,无法怀有经验地度过一生。我们无法娴熟自如地照顾病重的父母,也无法成熟轻松地抚养单亲的孩子。我们只能被“一个科学的、可被计量的体系”捆绑,又无精神寄托之所,只能在现世中受罪,呈现出疲惫之态。
同名短篇《缓步》中,台阶间有一条隧道似的缓步台,约百米,平坦而狭长,“左侧如悬崖,下面是无声的幽暗,另一侧是住户的北窗,拉着厚厚的帘布”。我们受罪前行,必然疲惫不堪,而上行的坡路中,缓步台可以作为缓冲地,让我们在调整呼吸与步伐的同时,回顾过去,看清将来。
班宇似乎无意书写时代,也无意为角色立传。他的角色始终在反抗命运的偶然性与人生的虚无,可以说,他更关注在困境中迸发的人的精神。疲惫的中年人仍竭力浮出水面,卧室的床在上升,地下旱冰场在上浮,植物沙沙向上生长,人在海中向上浮游……这些疲惫之人甚至要用削尖的钢尺刺破黑暗,飞跃深渊。因而,班宇赋人以羽翅,让人穿上旱冰鞋,令人幻化为鲨鱼,遇到游泳的独角兽,同时伴有大量富有冲力的动作:“展出锋刃,向着这片透明刺去”“在人群中加速前进,竭尽全力”“扎进前方的人群”“穿过夜晚的风暴”“倏然加速,凌入空中”。
人生一路上行。或许,步入中年的西西弗斯从未曾将巨石推上山顶,也从没有人见过他在巨石滚下斜坡时轻松地奔跑,或见到山谷野花时惬意的微笑。更有可能的是,巨石到达山顶后,即刻顺势从崖上坠落,西西弗斯和我们只听到轰然碎裂的声响,眼前除了茫茫无际的天空、海洋,就只剩下无尽的悬崖和深渊。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步入中年,周身困顿,思想胶着,这也是我们需要在缓步台上喘口气的时候。
编故事
班宇在《气象》中写道:
人和词语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悬在空崖,蹈于虚岸,既不可前进,也无法后退;写下来就是专断、冒犯与责难,不写的话则是隐瞒、背弃和欺骗,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一侧悬空,一侧屏障,可见词语和缓步台极为相似。
在这本小说集中,班宇继《双河》《山脉》等先锋探索后,又一次深入了以写作反噬写作本身的险境。他试图探索人与词语的关系,用语言捕捉逝去之物。因此,这些小说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故事结尾,也没有标示故事结局的定格画面,更多是夏加尔风格的诗意的隐喻,将我们带入无法言说之境。
《于洪》是书中唯一可勉强看作“东北故事”的小说,而结尾部分“我”和三眼儿的对话却展现了现实与虚构的对弈。“我”的叙事是虚构,三眼儿的推测是虚构之虚构。因此,同一个文本中出现了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一端讲述中年人面对工作与婚姻时的疲惫,另一端则是陷害与复仇的都市传奇。
这似乎是班宇对“东北作家”标签的反驳,也是对小说家作为“写故事的人”的反叛。我们越顺着三眼儿的思路想,就越能找到对他有利的论据,越觉得他所言为真。我们习惯按传奇故事的模式来解读人生,而生活更多呈现的却只是支离破碎。所以,“我”说三眼儿在“编故事”。书中说,此类模式的文本更接近数学公式,或一道条件不充分的证明题。
其余几篇的探索更为冒险,也更为精致、深刻。《透视法》中,“我”和网友见面,是虚构与现实间的相互倾斜与反噬,“我”怀着虚构之心步入现实,却被现实裹挟着遁入更深的虚构中。《活人秘史》中,小说家“我”的写作与记者C的写作同时进行,二人在彼此笔下生成,相互纠缠、疏导与劝慰,吞噬彼此,又融合为一。《气象》则进一步展现了作者、叙述者、角色间的僭越,“我”的叙述与《山脉》互文,二者环环相扣,像蛇反噬自己的尾巴。
《活人秘史》中,音像店老板认为,音乐是你感受到,而非知晓的东西。他由在中国迷路的经历意识到言语的局限,而言说行为本身,作为一种仪式,反倒会促成交流。因为,言说,除了声音和意义,还会传达“语力”,比如惠特曼的诗本身就能传达原始、庄严、无愧的力量,跨语言亦可感受。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言语对话,而是彼此凝望与握手。随后,仿佛禅宗、俳句,万籁俱寂中,他听到清脆的声响落在枝杈里。回去以后,他丧失了对音乐的全部感官体验,从此向内退缩,聆听内心的沉默之声。
莫里斯·布朗肖说:“你要么注定沉默,要么只是通过一种永恒的错觉来逃离。”这实际上是人意识到自己无法准确描述世界时的绝望。“我”总是否定音像店老板的观点,认为他在音乐上的世界主义是一种“恍惚”。重要的是,“我”相信,能通过写作来捕捉世界的真相,因此“我”想“将所有的声音、情绪与所有的人,鸟语和车铃,黏滞的苦难,恨及其友,全部钉死在我的演奏里。”
班宇用演奏比喻写作,其终极指向死亡。我们凭借自身无法超越死亡,写作却可以让我们在循环之中上升。正如旱冰场里的Y所说,我们无非是燃料,“反复地行使与牺牲,执行或者审判,直至挥霍一空,全部的故事都在这种循环之中上升。”
在“我”的叙事里,记者C是“我”现实中遇到的人,C将“我”的经历写进文章,“我”以C文中的形象进入旱冰场,与Y相遇。与C相遇的经历都会写进“我”的文本,文本包含我的自述及与C的相遇,也包括文本中的“我”想写出此文本的想法。在叙事层级一次又一次的僭越中,叙述者不断自我指涉,创造人物也被人物反噬,二者相互抗拒也相互融合。
面对人生的“罪”与“惫”,我们精神无所寄托,未来也无所期盼,眼前只有无尽的中途。我们无法退缩着遁入内心,只能一往无前。文学与写作带给我们的,就是通过一次次僭越与自我指涉,让我们从当下之惫抽身而出,击碎虚无,凌跃深渊,超脱罪的轮回与诅咒。
所以,我们在书中也时常看到暖人心窝的一面:让命运和女儿紧紧相依而不需要成为什么,与相互关心的人去海边散步而不需要发生什么,去展开羽翅飞翔,去摆动尾鳍遨游,围绕不存在的中轴径自旋转,乘坐北上的列车去破解存在之谜……
此后,我们将会“掠过云雾,行于水上,将无声的黑暗遗落在后面”。
(转自《北京日报》,作者:阿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