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在汉藏之间》
加入时间:2022-03-31 11:15 访问量:6339 信息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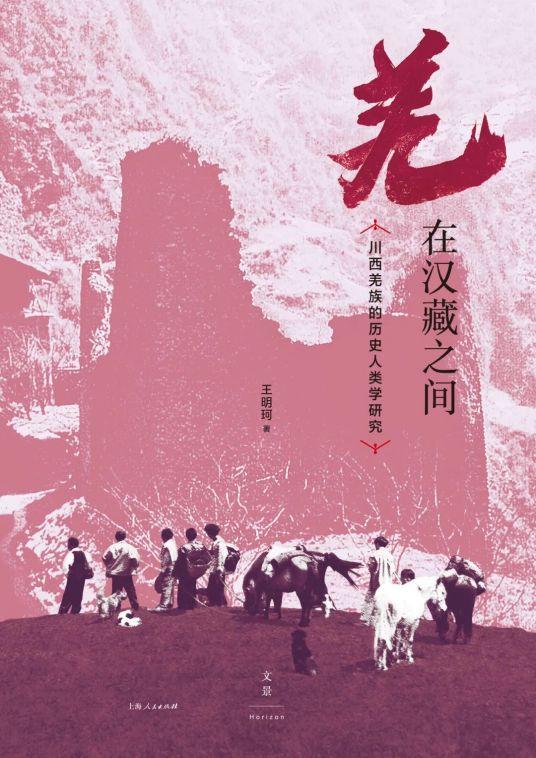
责任者:王明珂著
索书号:K287.4/2
研究中国边疆,就不能不提美国已故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虽然他自己本身并不认为是一个正牌的汉学家[ 参见[日]青木繁、江头数马编译:《中国天地》,每日新闻报社1973年版,第195页。],但是他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方面,可谓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因为他的中国边疆理论最先跳出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书斋式的中国史传统研究思维,转向研究边疆地区游牧经济存在的复杂性和合理性,广泛利用田野调查,试图用中原中央与边疆地区的互动去探索和理解中国内部文化和族群的多样性。这种研究思路直接影响到后来美国的学者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以及中国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他们在拉铁摩尔的研究思路基础上对中国边疆研究同样做出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因此建构现代中国边疆理论,就必须正视从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这些近百年来自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学者们的贡献,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与讨论。
治学研究方法的承继与突破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边疆主要有两种治学思路。第一种以国内的学者为主,可以称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天下大一统边疆观,基本思维方式是以国家统一为本位,从中原中央王朝的角度出发,注重利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学资料,将从内地中原到边疆各类族群视为一体的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文化的民族——中华民族,并以此为基点将历史上的中国边疆视为中原儒家文明发展的边缘地区,将现代的边疆视为现代化开发进程中的不发达地区;第二种思路以西方学者为主,他们利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解构当前来之不易的中国人的认同,宣称中华民族只不过是近代以来中国国族建构过程的结果,是汉族精英分子想象下的集体创造,因此中国的边疆只不过是汉族霸权主义对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的统制,助长分离主义,强化边疆族群差别,企图将边疆分离出中国。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观与上述不同。首先,他并不是把边疆与中国割裂开,而是将“边疆”的观念置于中国史研究的整体范畴,明确地认为西藏、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曾说过“美国关于中国完整的观念是:西藏、蒙古和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炮制了一个“满洲国”,意在国际上掩盖中国东北地区实际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和占领下的事实。拉铁摩尔非常客观地指出:“所谓‘满洲’是外来名字,中文没有合适的翻译,它的产生是由于19世纪后半叶,若干国家在政治上企图侵略中国,首先将东北地区看做一个完整区域而以满洲称之。”[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而“所谓‘满洲国’,不用说比‘满洲’更为牵强。它是两个中国字的结合,意思是‘满洲人的国’。但是这既不是中国人专用的名词,也不是从满族所用的名词翻译出来的,它完全是侵略者所用的侮辱性名词,是想回避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满洲’原来是一个地理名词,‘满洲国’则是一个政治虚构,它强迫东北民众承认其被征服的地位。”[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拉铁摩尔的将“边疆”纳入中国史研究的观念,得到东西方学术界的共同认可,后来的巴菲尔德、狄宇宙以及王明珂等人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也承继了这一思想。
其次,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和现代的人类学研究理论的运用。
中国国内研究边疆史的学者们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注重运用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史学资料,甚至将史料作为研究边疆的圭臬,但是他们恰恰忽视了这些记载历史的史家们的哲学观和民族观。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史家大都接受了儒家思维的高度训练,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是用道德理想替代社会实际,而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边疆可以说大都缺乏实际的、准确的认识,再加上中原儒家文明早已自成系统,这些史家们基本上是用藐视的态度认知边疆地区的族群,所以“我们应再思考《史记》这本书及其内容表述的历史······是否能让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皆感到骄傲······对许多少数民族而言,《史记》始于黄帝的历史叙事可能事不关己,其中北伐匈奴、南征蛮夷的记载更难以让他们感到光荣······当代中国人已非‘夷戎蛮狄’环绕下的华夏,而是约12亿汉族与55个共有近亿人口的少数民族所构成的民族,自然这样的历史书写与相关的历史记忆已无法正确、充分描述‘中国人的历史’,更无法让所有的中国人满意。”[ 王明珂:《反思性研究和当代中国民族认同》,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西方部分学者研究中国边疆恰又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以“纯学术”的理由,罔顾中国悠久的历史,用一些后现代的话语去解构中国的边疆,但是这些学者似乎没有考虑过这种解构是否会助长中国边疆的分离主义危机,是否会消解来之不易的中国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中国人”的认同,甚至也没考虑这样的解构会对边疆和谐的民族关系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因为中国的边疆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更是一个对人类社会现实关怀的问题,只有怀着为未来人类现实福祉的情感目的去研究中国的边疆,才能得到真正的新解。
拉铁摩尔本身就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甚至连大学学位都没有,仅仅于1928——1929年在哈佛大学接受了8个月的人类学的学术训练,后来竟然成为美国著名学府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 University)等大学的教授和研究中国边疆史的权威,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实地调查积累出来的经验。使他在学术界上崭露头角的第一部著作《 通向土耳其斯坦的沙漠道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就是1926年至次年10月跟随骆驼商队从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到克什米尔的考察记录。此后十多年,他又先后考察了新疆、内蒙和东北地区,成为“唯一一位曾在内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广泛游历的美国人。”[ [日] 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1944年5—6月,他又作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使团成员访问苏联和中国,并借此实地考察了西伯利亚、中亚细亚等中国边疆的另外一侧的广袤地区,这使得他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去研究中国及亚洲的历史与现状。其学术研究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本身就是他多年游历和实地考察的结晶。
注重实地考察也是巴菲尔德、狄宇宙和王明珂与拉铁摩尔相似的特征之一。如果说学术界对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素养有所诟病的话,而这些受拉铁摩尔研究影响的后继者则都是书斋式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非常好的学者。巴菲尔德在哈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训练,目前为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是享誉世界的人类学学者。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实地调查(field work),他对游牧民族内部社会运行的深邃理解还在于他曾在中亚的游牧社会实地考察多年。因此他的名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在学术界评价甚高,甚至被认为是形成中国“边疆范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 参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载《文汇报》,2007年5月25日。]。它利用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设计出一种游牧帝国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全景式分析框架,参照历史文献、碑铭的转述和边疆民族的语言,辅以社会学和考古学的视角得出了一系列的合理新解。[参见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载于《读书》2009年第4期。]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否定了长期桎梏我们头脑的一个观念,认为游牧不一定落后于农耕,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也有强大的影响。[ 参见[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序第4页。]可想如果著者未曾在游牧社会生活过,是无法体会和理解草原“人、草、牲畜”三者之间天然而巧妙的互动关系,也必然难能得出上述的新解。
巴菲尔德的弟子王明珂则从内心就不认同没有实践调查的文本分析(textural analysis),“这或许是由于当代许多人类学与历史学皆不相信有一套‘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掌握社会真实或历史事实。”[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既为了反思典范的边疆学与民族学研究,更为了在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促进公正、和谐与合作共生的民族关系[ 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6页。],他真正深入到北方草原、西南羌寨以及河湟谷地等地,用人类学“他者的眼光”去感受处于不同汉族聚集地区的少数民族社区。其田野笔记展露了多年田野调查的心路历程,“面对真真实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于是此后到2003年,这十年间,我每年都在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在真实的“人”与“社会”面前从头做一个学生。”[ 王明珂:《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自序第2页。]正是由于多年的实地调查,他能够真正从书斋式的思维跳出,去理解真实的边疆社会,“在得到博士学位后的十年间······拖着已届中年之躯到处翻山越梁子探访羌族村寨······事实上,我从羌族那儿受到再教育:没有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没有一种各地羌族能用来彼此沟通的羌语,也没有一种共同的羌族文化。羌族似乎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嘲弄着刻板学术方法与知识的虚妄。”[ 王明珂:《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5页。]
再次,从游牧生计方式的角度去解读边疆,是拉铁摩尔、巴菲尔德以及王明珂中国边疆理论的重要特色。
以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为本位的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对生产方式的演进的认知一般都是单线思维,认为农耕生计方式对于游牧生计方式是一种进步,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曾说“从物质文明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重要问题》,载《梁启超文集》,陈书良选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页。]无独有偶,著名学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也认为:“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渐进于游牧的生活,由游牧的生活而进于畜牧生活,而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生活,机器工业的生活。”[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他们以此类推认为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汉族在文化上就优于生活在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相对游牧文化······,钱穆认为农耕文化则是一种和谐而美妙的文化。”[ 启良:《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0页。]梁启超更甚,“胡元之篡,衣冠深炭,纯以游牧水草之性驰骤吾民,故九十年间,暗无天日。”[ 梁启超:《论私德》(节录),载《梁启超文集》,陈书良选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如果将拉铁摩尔的著作与传统上只重视农业社会的边疆史研究著作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拉铁摩尔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起源同在一个上古时期,一切文化都同样原始,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资源的不同,在文化表现上存在若干差异。”[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所以在拉铁摩尔的研究视野里无“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孰优孰劣之分,游牧民族和汉族在文化上是平等的,中国的边疆本质上是游牧民族与汉族共同“经营”的边疆,虽然这种经营时常伴随着暴力。拉铁摩尔还深刻地指出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游牧社会完全不同于农耕社会,两者很难融合,处于两种社会的人也很难互相理解,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儒家文化在内地汉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游牧社会影响就微乎其微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唯一可以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和以畜牧为主的社会是工业化。”[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其卓越的洞见。
巴菲尔德继承了拉铁摩尔文化生态的理论,将边疆地区分为四个关键的生态与文化区域,即蒙古地区(Mongolia)、华北地区(north China)、东北地区(Manchuria)以及西域地区(Turkestan)[ 参见[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并从自然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出发,认为游牧生活是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内陆亚洲草原的主导性生活方式。他曾在中亚北部阿富汗游牧民社会中作过长达两年之久的人类学考察[ 参见[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2页。],熟知游牧生活,从游牧生活的特性出发解读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结构和草原的游牧制度,又通过人类学的研究观感以及对历史文献进行的分析,得出游牧的生计方式,“其经济建基于游移不定的游牧生活之上,这些经济特征在于这些民族散布于广阔区域之中,在苍茫蓝天下搭帐而居,以肉、奶为主食,崇尚军事冒险与英雄般的个人成就,可以说,这些骑马民族与其汉人邻居截然相反”[ [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所以“对于定居社会的历史学家而言,就算怀着美好的心愿,也总是难以理解那些与其自身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生活方式的部落游牧民族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 [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除了系统地学习游牧社会的理论研究成果并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王明珂还在近二十年里在内蒙古、四川、宁夏、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做了长久而深入的田野实践调查,所以在他眼中,“‘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与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相似,他也认可游牧生计方式是由特定环境决定的,不是人类文明史上“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也并不落后于农耕生计方式,而是与农耕生计方式一样,是人类为了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致的经济社会体系[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王明珂依据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将北方的游牧人群体分为三类:草原游牧的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以及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和鲜卑。在他看来,中国的边疆就是处于中原地区的汉帝国与这三类游牧人群体的互动共同构建的,甚至是后来在边疆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其实都可以追溯至形成于汉代的这三种游牧人群体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模式中。
从拉铁摩尔到王明珂,他们解读中国边疆的一大贡献就是从实地考察的方法真实地恢复了游牧生计方式以及游牧社会的历史主体性表征,认识到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在中国边疆史的构建中都具有主体性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边疆确切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互动而建构的边疆,游牧社会与内地的农耕社会是一个有机而不可分裂的整体。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在边疆资源上虽然有竞争,但更多是共生、互补与融合,这种“共生互补”的关系为研究中国边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另类视角的启示
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服务于现实的,边疆研究也不例外。当代中国的边疆问题,主要是如何合理、和谐地建设一个稳定而繁荣的边疆社会。拉铁摩尔等人的中国边疆研究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的边疆从古至今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建设的,他们分布聚居于边疆各个地区,所以建设一个和谐而繁荣的边疆社会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和别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十分服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既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等有强烈的认可,也有包容、忍耐、与不同于己的族群有和谐相处的心态,同时能进一步能尊重、欣赏不同于己的族群的文化,这样才能理解别人之美,更能使别人之美得以有各自展现的机会。这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理念也是中国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延续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长此以往甚至可以成为世界各个族群和谐相处的文化典范。
从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这些学者都认为中国的边疆是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互动构建的边疆,边疆之所以互动而非一统的根本原因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与游牧为主的社会不兼容。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蒙古经济和中国经济并不一定是敌对的,在现代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为用。过去所缺乏的是一个良好的协调办法,而现在,工业和机械可以联系草原与农村,联系矿区和城市······他们可以很融洽地合作,而不是一个民族臣服于一个民族。”[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随着工业化、科技化、信息化时代的逐步演进,当代中国边疆的核心问题就是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通过经济发展奠定充分的物质基础是建设和谐而稳定的边疆社会的首要条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边疆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边疆地区发展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因此支援边疆建设时,应该再一次回顾邓小平同志多年前的警告:“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边疆地区的建设一定要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有耐心、有规划地干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才有可能真正地将边疆变成和谐、稳定而繁荣的地区。
如何发展边疆社会?美国社会学家赫克特(Michiael Hechter)对少数民族聚居经济条件较不发达的“边远地区”提出了两种模式: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Internal colonialism Model)。扩散模式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过程中,经济较发达的“核心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逐步扩散到“边缘地区”,并使“边缘地区”在社会和经济上各方面都与“核心地区”发展水平相差无几,最后各地区富裕程度平等,文化差异失去社会意义;内部殖民主义模式则是不同的发展方向,核心地区被认为在政治上统治边缘地区,在物质上剥削边缘地区,就像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一样,只是对象是本国内的边缘地区和少数民族,内部殖民主义模式不认为工业化将导致民族发展。[ 参见M.Hechter:《内部殖民主义》,载于马戎主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90页。]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民族改革,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以及医疗发展都给予了大量物资、人力和财政支持,有力地推动了边疆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积极扶植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事业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汉族地区的政治行政制度、经济管理制度、教育和医疗体制等也逐步“扩散”到边疆地区,所以中国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毫无疑问是属于扩散模式。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在我国也是由来已久,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国内各个民族排列在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序列中,在各个民族之间努力划分先进和落后,甚至认为国家对边疆的各种支持是生产力发达的先进族群对生产力落后族群的怜悯,不仅忽视来自“边缘”的声音,往往还对边疆地区的人们采用一种落后刻板的歧视眼光,这种被拉铁摩尔称为“亚帝国主义”的思想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国家对边疆的建设与开发,因此防止边疆建设滑入“内部殖民主义模式”是未来建设和谐、稳定的边疆社会最重要的任务。
从拉铁摩尔到王明珂的这些学者们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们解读中国边疆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现代西方人类学“参与者观察”实践认知的方法,而非用某种“科学”的理论去指导,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要了解一个和自己所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不能只依靠理论分析和数据推理,不然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自我想象的构建之中,这种自我想象的构建可能会完全曲解我们想要了解的真实社会。黄宗智先生就认为这种西方人类学的认识方法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从事物的“感性认识”出发,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来指导实践,即实践——理论——再实践。[ 参见[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笔者认为这种西方人类学“参与者观察”的方法不仅仅对研究中国边疆有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论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条化、书斋化,以及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甚至可以进一步思考,理解迷局一般的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参与者观察”的实践认知出发而不是从某些经典的理论预设出发,通过对中国各地不同社区的实践认知做深入地调查研究,熟悉这些社区的内部逻辑运作,再与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参照和相互作用,来建构真正的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概念,从而验证和说明中国各类社会实践,理解现代中国。
另类视角的不足之处
从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这些学者在对中国边疆研究有着杰出成就的同时,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研究缺陷。其一,他们虽然都认为中国的边疆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动建构而成,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影响整个二十世纪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的影响,不约而同地认为汉族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甚至对边疆少数民族而言是统治民族,都在一定程度上隐晦地指出是汉族的命运主宰和决定了中国边疆的各个时期。例如拉铁摩尔认为游牧民族事实上是被中国北部采用较高农业经济的中国人排斥出来的[ 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甚至在其著作中将汉人进入边疆,称为“侵入”。巴菲尔德则认为是中原王朝的兴衰成败决定着边疆游牧民族的命运发展,而王明珂也部分地继承了巴菲尔德的这个理论。
其二,他们对中国边疆的观察和研究也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观念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将汉族和边疆游牧民族作一种二元对立的预设,即更重视农耕的汉族与游牧的少数民族的冲突而忽视两者之间的合作。这种二元对立的预设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历史上已经沉睡的族群记忆,使自己族群那些曾经令他们感到荣耀或屈辱的事件不断得到回忆,却容易让他们忘掉历史上更多的是族群之间的帮扶、合作与温情,这种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忘却有可能会对今天边疆地区民族间的和谐共处有些许不利的影响。
其三,笔者十分赞同这些学者重视“边缘话语”的价值取向,即王明珂所言:“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术的和文化的)产生反思性理解,”[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自序第3页。]但对“边缘”这个概念存有异议。
所谓边缘,就是非主流。无论是“华夏边缘”或者“兄弟民族”[参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版。]的构建,都默认边缘与主流是有一定的距离,族群之间互有差异,有轻有重,边缘不会成为一个国家的主体构成部分,族群间的差异则会固化,边缘到永远。另外“边缘”这个概念还隐晦地指出作为边缘的族群曾经是遭到过主流族群的排斥和打压,如今对边缘的重新建构很容易唤起作为边缘群体的历史意识和自身的民族意识,如果纵容所谓“边缘群体”各自无止境地自我文化认同,毫无疑问,在未来有可能导致族群间的剧烈冲突,不利于在“扩散模式”的组织框架下实现对边疆社会的整合,所以这种“边缘话语”可能是对边疆的历史是另一种角度的阐释,但边疆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民族团结是一种现实关怀,这种边缘话语就颇显尴尬。
当然,“扩散模式”对边疆社会的整合也不是否定各个族群的多元文化,特别对于那些人数较少,无文字,处于现代化发展弱势地位的族群,还要采取文化保护。这就有一个问题提出:边疆研究的终极目的和现实关怀是什么?笔者认为,如何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深深地植入边疆社会是边疆研究的最终目的和现实关怀。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被世界所认可的主权国家,在这片国土生活的人,无论是何种肤色,讲何种语言,归属于哪个群体,只要拥有这个国家合法公民的身份,就没有“主流”,也更没有“边缘”,都属于“中国人”。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就必须认同自己祖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以及历史文化传统,这就是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国家着力对自己国民培养的国家认同。人们只有将国家认同确认为自己的最高层次的认同,并了解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真正地关心国家,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自愿挺身而出,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个人的感情也随之受到伤害,并会主动为国家的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这也是建设和谐、稳定和繁荣的边疆社会最根本的保证。
四、结语
虽然有些许不足,但是瑕不掩瑜,从拉铁摩尔到王明珂的非中国传统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对边疆研究的另外一个视角让我们正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中国的边疆是由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建构的边疆,至今边疆社会仍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在一起生活。他们从游牧少数民族的角度去思考边疆得出的种种震撼性的理论阐释,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以往从农耕汉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边疆观的种种理论预设是否可取;曾经的边疆研究是否真正的关注和了解作为构建边疆的另一个群体,即边疆上的少数民族?
“文化中心主义”边疆观对我们的思想禁锢已久,我们现在有关边疆的种种知识来源仍来自历史上的“经典著作”,而不是来自对中国边疆社会的实际研究调查。从拉铁摩尔到王明珂的这些学者们给我们一个方法论的视角,即现代西方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这个方法论强调对边疆不同社区一定要做深入地调查,然后对每个社区进行全方位地比较观察,在比较中发现,再从事实的发现中总结,然后从总结中形成某种经验性的理论准则,再用这个理论准则去验证实践,这才有可能看到真相,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边疆和解读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