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纪年》
加入时间:2023-01-20 15:20 访问量:4370 信息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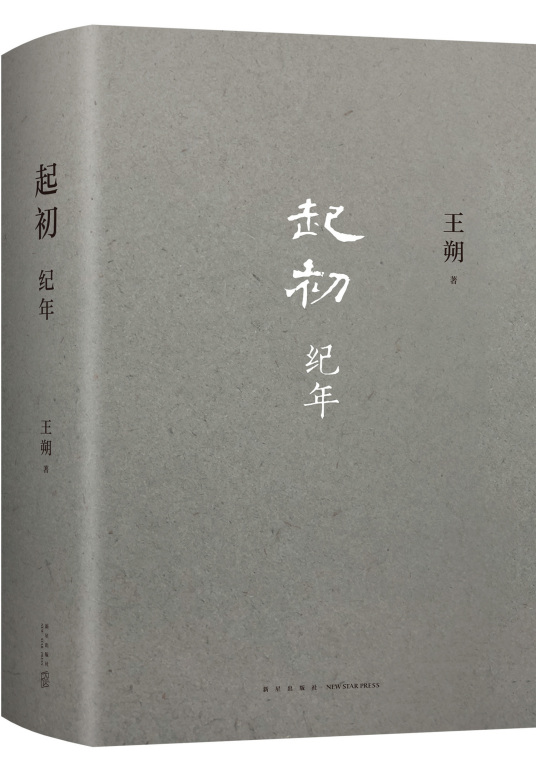
责任者:王朔著
索书号:I247.57/26380
1
当年影视圈里传的最邪乎的神话之一是《天下无贼》剧本怎么改都不合格:一对男女贼搭档由“坏人”突然变成“好人”,心里动机是啥?据说京城的著名编剧挨个被接到剧组开会,每人都是信心满满地进去,挠头皱眉着出来,最后只能把王朔请来,他大致听了听剧情撂下一句话:让那女的怀孕!然后一切忽然就神奇地都讲顺了。
这个传说的可信度百分比无法确认,但是它或多或少印证了王朔在二十年前的电影圈和文学圈无人可比的标志性能力特征:他可能不是视野格局最宏大也不是思想最深邃的那位,但他的穿透性洞察力是彼时整个中国以写字为生并谋利出名的那一大群人里最出类拔萃的。如是能力建立在他与众不同的成长背景和个人体情感体验经历上,它们赋予了他一个旁人非常难拿的审视周遭世界的位置角度,同时又滋养了他敏锐犀利而直指人心的表达方式。
当所有人都绞尽脑汁地在善恶道德层面上对人物进行翻肠倒肚的“搜刮”翻转时,只有他能跳出这个思路,从人物的生理变化引发心理嬗变的角度对整个剧作构架致命一击。这背后包含的王朔式潜台词是,让人物回归属于人类本性的一面,吃喝拉撒睡、结婚、生子、忙碌、欲望、衰老、死亡,而不是待在所谓的精英们为他们勾画的道德伦理框架中用非人的思想和行为逻辑去伪装成活人。
如果明白了王朔的如是思维习惯(这一点从他八十年代跨入文坛开始就从未改变),就不难理解《起初·纪年》在常人看来不伦不类插科打诨四处走神的文体其出处所在:从根上王朔就不相信历史上的王侯将相长孙公主们都是长篇古装电视剧里那副嘴脸——除了唱戏式的甩袖作揖就是之乎者也的虚词连篇。他们也都是抠脚钻鼻,洗澡搓泥,坐在马桶上遐想事后烟的人类,这和挥斥方遒南征北战成就千秋功业和万世英名并不矛盾,借用他早年在小说《顽主》里写的一句话:孔雀开屏是好看,转过去就是屁眼儿。
那些对讲述汉武帝跌宕起伏人生的《起初·纪年》里充斥着北京片儿汤话,各种时空穿越的名词和动词(股份、公司、手刹、人身攻击、酒吧、夜总会、料理、专项债、耍流氓等等)和通假错别字(墙裂(强烈)、湿妈(是吗)、逮摆(得把)、聊骇(聊high)等等)一万个看不顺眼的读者们,或者那些对书中人物操着京腔讨论汉朝国家大事感到颇为冒犯的人可能没意识到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和人物行为言语规范正是本书所意图唾弃的。但另一方面,沉溺于北京方言的街头话语逻辑不能自拔也并不是王朔的首要目标,他想要做的,也正是他在四十年写作生涯中从未放弃过的,是想尽办法用独辟蹊径的话语方式颠覆读者对非人崇高的错觉,用他认同的表达逻辑推翻被精英定为规范的尺度框架,把知识分子们认为不能颠破的先验真理拉下神坛。为此,他不惜让一切都走向表面上世俗不屑的另一个极端。有点像一个故意考试不及格的孩子对着满分答案淬了一口吐沫,转身扬长而去在老师家门口撒尿和泥的姿态。《起初·纪年》中的这种行文方式挺颠覆,非常任性,甚至读起来过分到了有些故作姿态的装腔作势,但这就是王朔标志性的逆行于众人并乐在其中的差等生满足欲,也是他这些年来依然不断萌生写作快感的源泉之一。
2
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王朔就在访谈中抱怨他遭遇的写作困境。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末尾的《跋》里,他坦白为了写某些固定类型的小说,他不得不一直在生活中“演”,以便“达到为自己的小说凑场景”的目的,因此“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诅咒”。如果翻译成常人能理解的话,就是对于以取悦大众为目的的写作,无论是写小说、电影电视剧本还是在那个年代引发大量公众舆论争议的杂文评论,他都烦了,腻了,厌了,不愿再为此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掏心掏肺,不愿为了单纯文字的出彩或仅仅维持自己的公共声名形象委屈自己。
他开始改变思路,把那些与现实勾连性搭边的,能让读者产生代入感的内容都毫不留情去掉。从《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开始,这种风格转变显得突兀起来:那些感性而细致简练的环境描写,带着距离感又温情脉脉的情感烘托和精心钩织的脑筋急转段子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时空坐标褪去,无目的无方向充满着语义甚至是语音随机联想碰撞如潮水般涌来的第三人称对话。无论是《谈话》还是后来的《我的千岁寒》,看了几十页以后,都会让人不由自主产生这是不是写得太匆忙来不及讲究格式和排版的剧本草稿的疑问(在《致女儿书》里,王朔曾正经提起过文字格式对写作自由的剥夺)。他对写在纸面上的文字内容和语感的看重,远远超过了先前为他小说带来无穷魅力的情绪氛围和跌宕情节。这种崭新进化而成的,拧开水龙头就卡住关不上式的哗哗流淌行文方式,大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恣意纵横感,为他随着年龄增长泛滥不止的对镜自我悲悯情绪提供了莎士比亚式的滔滔不绝展现渠道。
但王朔不愿明提的是,他并不是一个想象力凭空而生,可以超越自身躯壳去体会他者灵魂的写作者。他特别依赖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真实体验。那些在他过去作品中闪着天赋灵感光芒的片段,无论是在《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过把瘾就死》,还是在《我是你爸爸》和《看上去很美》中,都间接来自他在生活中“扮演”的真人角色。在他声名如日中天的九十年代,不断有人跳出来揭秘说王朔小说中的某个精彩部分来自于他们在饭局上的谈话,当大家围着饭桌眉飞色舞侃大山时,王朔一声不吭坐在一边掏出小本狂记。其他人兴高采烈的你言我语,成了他个人体验的素材,并由此发展出一个个栩栩如生如假包换的虚构人物。
与现实的切割也许解开了捆住王朔写作思想的绳索,让他在纸面上获得了极大的纵横驰骋自由,他由此穿越时空去给六祖惠能写传(《我的千岁寒》),凭空想象后宫中武则天的种种面孔(《宫里的日子》),甚至跨界到哲学界用语录体给唯物主义写起了史纲(《唯物论史纲》)。但内在,那份依托蕴藏在自身躯壳里的感受才能勃发的表达欲,那股依赖过往体验才能校准方向的情绪力量并没消失。只不过,与现实的联系不复存在以后,先前作品中隐去保质期的情感和迎合各种潮流的伪装都统统褪去,一个带着真正自我底色的王朔在潮汐退却后的岩壁中显露出来,并以不加修饰的姿态跳到了前台。
这就是我们在《起初·纪年》里读到的那些文字。
3
《起初·纪年》七百页读完,体会着汉武帝在作战室里和群臣开会听汇报,下命令多少万人走雁门,多少千量辎重车要渡黄河,怎么修路才能让部队过山口,敌手匈奴又是如何配备的人员装备,就会觉得这些唠唠叨叨又自得其乐的如数家珍莫名熟悉又亲切。
小时候也赶上了这样的时代末尾,路过院门口的水泥乒乓球台子,总会看到几个大孩子蹲在上面侃侃而谈:我军人数多少,马匹几何,车队多长,炮火多猛,深入战线后方如何与敌战略性对峙又怎样神出鬼没翻江倒海,指挥官又在何等困难压力下带领千军万马九死一生成就千古战功一世英明。它们可以当故事听,也能满足幻想欲,讲述者引经据典时而面色沉重时而又眉飞色舞的神态至今难忘。
搭配上所有人物如出一辙连珠炮一般迸出来的北京腔和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讨论军情的热乎劲儿,这《起初·纪年》里汉武帝和文臣武将的会议似乎跨越了两千多年来到了那些大院里夏日午后空无一人的球场。在那儿一群身着板儿蓝板儿绿(蓝色和绿色军便装)的少年在场边树荫下跨着二八自行车后座神采飞扬地谈古论今,从张飞关羽说到秦琼李元霸,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侃到攻克柏林,从诺门坎飞到三八线。这场景在六七十年代北京海淀区复兴路两侧高墙后的居民区尤为常见,那时能让这些整日无所事事的少年们操心的并不多,在热烈讨论中成为横刀立马号令天下的武将是最为炙手可热的梦想之一。
有点不同的是,绝大部分这些孩子成年后都热情消退,化身为普通市民被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婆孩子热炕头缠绕着日渐颓丧。只有王朔在拥有了难以置信耀眼的作家光环之后,又通读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多种佛经甚至是古希腊巴比伦两河流域历史,然后把它们一锅烩进这人物精神时空有些错乱的五十万虚构文字当中,让所有这些历史人物的名称都几乎退化成了空泛的代号,被平行世界里另一群在虚拟时空中长大成人走上风云际会历史舞台的少年身影所替代。
当你读到子夫小卫和大帝之间的煮粥斗嘴恋情,或者公主和栾大的关系曝光后被七大姑八大姨的指指点点,甚至是皇公贵族们火气上头的撇嘴抱怨,它们真的跳离了史书中空泛断裂的记载以及后人对其万年不变的模块化描摹,而几乎直接拐进了《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甚至是《父母爱情》这类长篇怀旧电视剧的人物话语调性关系和思维与行为模式(虽然更有可能是主观上照着《红楼梦》大观园里闲言碎语家长里短的机锋对话描的)。没办法,当王朔想让这些人物具有些日常生活细节的血肉和情绪,又不愿意嵌入任何一个既成规则框架时,他只能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情感的那个起点出发。
与当下现实的剥离似乎赋予了他展翅翱翔的自由,但他的直觉反应既没放在研习已久的佛经上和也不是读的滚瓜烂熟的历史细节,而是一头扎进了潜意识里最为之怀念动容的北京复兴路。在《起初·纪年》里,他替自己和儿时的伙伴们圆了那个指挥千军万马出生入死,或坚定不屈或忍辱负重或悲壮牺牲又最终名垂青史的宏大历程。但在建功立业的同时,和姑娘逗咳嗽,找对手耍心眼,吃香喝辣,摔脸子摆架子撂挑子这些日常琐事又一样不落,每一个细节都补全了他对昔日的少年们在另一个历史平行时空人生轨迹的丰富联想,都寄托了他不能撒手要永远抱着与之一同入睡的单向理想主义情怀。
在《致女儿书》的开头,王朔勾勒了这样一个让他魂牵梦系的场景:一个从远方休假归来的女兵,身穿着黄呢子军大衣披着肩章带着海军无檐帽从绿皮火车车厢里露出身子,跳下路基站台,圆圆的脸庞满心欢喜迫不及待。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带着强烈七十年代电影氛围色彩的画面看作是整个“王朔宇宙”中最闪亮夺目的一帧,但在它的前面和后面,还另有成千上万个画面构成了整部“电影”。它们也许不会像这个场景一样一直青春气息涌动光彩照人,也会有伤心失落、悲情失败、流血牺牲和孤独终老,但它们都内在贯穿着“火车女兵”式的夜空月芽儿欣赏型情绪内核。为了这一格画面在那块虚拟银幕上以最佳姿态锃锃放光,王朔会倾尽全力构筑一个关于它的文字宇宙。
《起初·纪年》(也许还有另外未出版的三卷)中绝大部分人物都确有其人,绝大部分情节也都有史书源头出处,这其实是替王朔省了大事。他无需另起炉灶费大劲去创造另一个宇宙,直接把胸中成型的人物和脑中萦绕的细节代入历史躯壳即可。想读二月河式对大历史进行国产报告文学式跌宕起伏式复述的人对《起初·纪年》通通都会失望,这里面根本没故事只有唠嗑流水账。它和《三国演义》《说唐》《水浒》式的历史传奇无关,而是汉武帝等人主演的一部五十万字《红楼梦》续集别传,在唠嗑之余圆的是那个多少年前在球场边树荫下对“火车女兵”及其构成宇宙的少年遐想。
4
但在实际阅读过程里,作为读者的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一个有些尴尬的迟疑:该如何把《起初·纪年》的语感和长篇评书或者单口相声(比如网上广泛流传的郭德纲那些“只挖不填”动辄长达六七个小时的段子)分开?抑或者根本就没必要区分?
第一和第三人称的故意混淆,口语化的跳跃、省略和情绪突兀表达,环境勾勒描写和人物行动叙述的缺失,以及旁白式编年体事件的大量堆砌都让《起初·纪年》和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套路(哪怕是网络文学)拉开了很远的距离。也许我们可以说它的文体无限贴近上世纪初的欧美意识流文学(八十年代一大批中国先锋作家对此进行过大量的模仿和借鉴),但真正读起来总会忍不住想,这恣意纵横的文字跳跃如果让郭德纲站在台上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讲出来效果会好上多少倍。那缺失的起承转合和人物心理起伏会怎样被表演者的姿态手势表情恰到好处地演绎填补,成为活灵活现的段落。当成严肃文学写,却一不留神完成了个七百页评书话本的文体错位尴尬,有可能会伴随这书的阅读体验相当长一段时间。
它由此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相比起王朔那些在三十多年前广受大众欢迎的通俗小说,这些不再以受众为目标,埋头只顾个人写着爽的文字究竟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要客观评价其实挺难。因为《起初·纪年》和王朔在《和我们女儿的谈话》之前的作品并不在一个序列上。在那些小说里,他的主人公永远是被甩出体制之外的待业青年,在身无分文之余还被简单纯粹的爱情所吸引,在对金钱、道德、知识分子式的精神崇高和市民阶层的市侩尽情嘲讽的同时,他又有简练温情让人动容的语言去描摹那瞬间闪过的激情。它们同时满足了几个不同阅读群体的需要:想要看最早一批文学搞笑段子的,想要在其中找到纯洁爱情的,想要透过颠覆式的浪漫文学语言去强烈批判现实并保有对消逝理想的忠贞的。
但所有这些都在《起初·纪年》中消亡了。当阅读快感在文体的剧烈转换和内容的线性流淌之间溜走以后,对它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对那潜在“王朔底色”的认可程度。让人感慨的是,那些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王朔作品中曾经收获的爽快、动情和犀利的批判意识最终都过了期。他自己都不再确信这些内容的现实价值。我们也终于明白他在剧烈的时代转换时爆发出来的中国嬉皮士式的批判姿态最终来源于与大众并不相交的特殊背景经历而造就的审视角度。于是在偶然同行了一小段以后,他和曾经为他叫好的读者们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
不过,尽管二十年来王朔对金钱、名誉、声望都不屑一顾,但他在过去积累的名望气场却还在不为意志为转移地持续把《起初·纪年》托上关注度的顶峰,就像曾经的北京复兴路两侧高墙内的苏式建筑群在头脑里被动留下的不可磨灭印记。
也许那才是王朔的真正底色。其后无论发生了什么,友情、爱情、伤感、喜悦、家庭、子孙、黄金万两还是孤独终老都没法改变它的单一质地。他越沧桑就会越觉得这颜色鲜艳好看纯粹动人完美如初,也就越想自制一副这个底色的太阳镜戴着以孤芳自赏出淤泥而不染的壮阔高姿态看穿全宇宙。他获得的解脱越彻底,就越忍不住想去吮吸那与生俱来的胎记,幻想从中找回视之为珍宝的出生之际母体沉浸体验感受。
究其本质,《起初·纪年》正是以刻画这个感受为目的而诞生的。
作者:九苍(来自豆瓣)